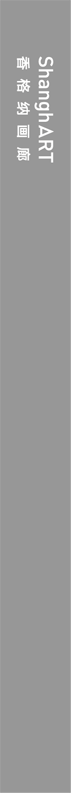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4-03 11:38
序 言
艺术项目《滞留》(“Suspended”)是艺术家将一个项目同期分置两地来实施和完成的行动。 该项目以北京-香港双城镜像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有关物质、物质流动和现代性空间秩序讨论的剧场。
之所以将该项目称之为“行动”,是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变化和调整的博弈状态,而并非只是一个既定方案的执行。在项目之初,艺术家意图在两个城市“互赠花园”。所谓花园,实际上是分别在两个城市截取出数方土壤,并提供与土壤相同属地的河水用于浇灌。在互赠之后通过精心的照料和阳光的照耀,让埋藏在土壤中的野生植物和种子在对方的城市中生根发芽、长成一个花园。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了解到,无论是土壤、河水还是种子,在通往两地的海关条例中均属于被禁运的物质,花园作为美好的象征最终只是美好的想象,而展览就像本该丰盛的餐桌上只剩下了餐具:一个彼岸的空箱、一个此岸的底座和一堆细如发丝的棉纱。
自然物中最原生态的土壤、河水和种子,这些原本属于自由流动的自然物质,在当代文明管控体系中被异化为"特殊物品",在海关条例中被“禁足“,人类文明与自然有机物之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这个项目不只是单纯的地缘政治的研究,而是一场关于物质本体论的讨论。
空 箱
因为花园的缺席,箱子便只是空箱。来自香港的空箱在北京香格纳画廊露天庭院中的禅定状态与来自北京的空箱在香港The Uncommon室内空间中卡在门框的悬停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两个城市截然不同的气质:一个是稳重的,秩序的;一个是喧嚣的,纷繁的。而卡在门框的状态非常生动的回应了该项目的名称:滞留。卡在门框的木箱,它同时也卡住了从室内展厅通外室外庭院的路径。
当自然物被归类和审批,空箱便意味着不再承载标准化的1m³容积幻想,它被排除在全球化物流体系之外。被空置的箱体内部空间,实为被禁运物质反向填充的居所———一个无法被系统捕捉的符号性存在,它成为所有受阻物质的集合。因此,空箱之空也就不再受箱体的定义和束缚 ,空箱从而转化为“空相”——“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无目的、无终点的永恒流动”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种超越实在之物的想象振动。
底 座
底座原本是为了承载对方城市赠送的花园,但此时的底座也只是空的底座。由香港制作的底座卡在香港展厅的门缝间,上面有喷漆的文字。喷漆的繁体中文“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出自佛教经典《金刚经》,大意是没有一个地方来,也没有一个地方去。这句“如来”的禅语恰好释怀了在项目之初花园落空的沮丧,也更好地填充了项目最终呈现的“空相”——只有文字的空的底座反而更好地将观众的凝视引向了物质的缺席。当"物之自在"不在,“空”便成为一切潜在戒律的证物。尽管来去之路被阻滞,但谁又能真的抑制得了来去呢?在意识之中,在意志之中,在空气之中,在风的侧翼,来去自如。与中文对应的英文翻译是“No Origin, No Destination”,翻译落脚在全球化物流体系中两个最核心的词汇上:“始发地”(Origin)和“目的地”(Destination)。当“乡土”流动遭遇系统“禁足”时,这句翻译便成为所有受阻物质的辩护词,也是将项目从禅宗拉回现实的互文关照。
而北京制作的底座在北京展厅中是平放于香港空箱一侧的,保持了它该有的矜持与安定,也保持了简体中文的制式。底座上依然是空无一物。
棉 纱
与“极少”的空箱和空的底座相反的是“极多”的棉纱。 棉——这种曾推动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的植物,曾驱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白色黄金” ——还原为前殖民时代的植物本体。棉纱诉说着香港在英殖民时期的棉纺织业历史(香港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基地)。微妙的是,紧邻香港展览空间的街道也叫“浣纱街”。作品中使用的棉纱是未经漂染的手纺棉纱,不同于工业化的漂白和修饰,棉纱的天然色泽和纺纱过程中的指纹和汗液被刻意保留,并以手工缠绕为“8”字环的方式加以固定。在香港展厅中呈现为码头装卸货物的捆扎方式,在北京展厅中则呈现为三摞“棉山”的连续堆垛。如果将展厅中的棉纱首尾相连,每个展厅的棉纱长度分别是两地陆运距离的量化:2,222,000米——一条漫长的路。在如此庞大的数字被视觉直观化的同时,即是该项目遭遇制度性限制的图像生成,也是标准化的物流计量体系和生产者不可量化的身体时间性的解构。
颜 色
在北京和香港两地的展厅中都出现了淡蓝色和浅粉色。在北京展厅中是两摞两种颜色的纸张以手撕日历的方式挂在墙上,在香港展厅中则是把这两种颜色直接刷在了墙上。这两种颜色来源于物流运输中票据联的红蓝二色,也对应了两地人口通行的证件颜色:大陆到香港的通行证是淡蓝色,香港到大陆的回乡证是浅粉色。在香港展厅中,两种颜色的墙上分别用纸胶带粘贴了“LOOK RIGHT”和“LOOK LEFT”的字样,这是在香港路口的地面上一定会见到的提示:“望右”或“望左”。 使用纸胶带替代了印刷字,强调了某种临时与修正。同样地,香港路口的交通信号声也被挪用到了展览之中,这声音代表了“滞留”的另一种现实投射:在交通信号声响起时,要么是人被滞留,要么是车被滞留。滞留不只是暂时性的存在,相反,它漫长而永恒,当一方流动时,另一方就会被滞留,如此往复。在北京展览中用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声音:展厅单向进出,展厅出口每十分钟开放一次,意味着观众至少会被人为滞留“十分钟”。每间隔十分钟,出口处会响起一阵短促的闹铃声。
尾 声
是滞留导致了花园的缺席?还是花园的缺席产生了滞留的状态?亦或是对花园的想象制造了滞留的困境?也许它们互为始发地,也互为目的地。而滞留在此时便不再是滞留,它就是流动本身。
Related Exhib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