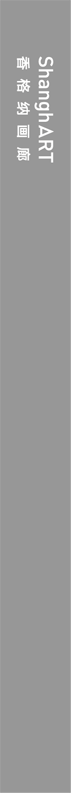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9-18 16:53
他的作品并不甜,也毫无意愿取悦观众,倒不如说就像一声惊雷,非要把你吵醒不可,或者就让你身处废墟,让你觉得生活与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吕澎
“胡项城作品展:眼前的远方”已于10月16日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幕。展览从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出发,把各种日用品、废弃物、垃圾和雕塑、卡车、脚手架等结合起来,用大型雕塑、装置、影像等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表达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危机重重的现状到对未来远景的推想。
生活世界的重构——胡项城的艺术
那是在罗马,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面对胡项城,他的水泥、木板、钢筋、砖块、卡车、涂料、形形色色的现成品和废弃物,你轰然觉得自己来到了杜尚开启的乐园,你的脑海中闪回着达达主义宣言,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阿尔普的垃圾,施维特斯的梅尔兹堡,还有一长串这些被宠坏了的反叛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姓名。现成物,垃圾,“低贱的” 材料,所有这些反艺术的疯狂举动,在今天已经对我们露出了柔和而富于诗意的展示面,我们渐渐地将它们抛光上油,不再为这些事物和历史感到惊奇。艺术家拥有无限的自由,和那个时代相比,刺耳的噪音在一次又一次的修音下已经成为值得被聆听的美妙音乐。
逐渐的,我们变得不再关切雨果·鲍尔在瓦格大厅公开宣读达达宣言时的刺激和压迫,那一代颓废青年艺术家的原始冲动和象征性的挣扎。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叙事中淡化最初的绝望——然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绝望感时刻潜伏在生活中,它随时将要瓦解我们误以为坚实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正是由我们一度坚定的想象所构成。
胡项城出生于1950年的上海,他的字里行间总带着一种从瓦格纳那一世代所弥漫的总体艺术的气质——这当然与他的职业经验有关。这种气质是开启式的,正是由于某种绝望和希望并存的时刻,激发了艺术家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幽思。胡的早期作品中,对抽象的人类共同体的关切已经出现,例如1985年的《心像图》,由胡项城、蔡国强合作,用油色、布、绳子陶土创作的综合装置,以及《第一声雷》系列铜雕作品,在浅浮雕效果上创作出拥有原始主义面孔的人类形象。
孔伯基在《看胡项城作品有感》中引用胡项城的自白:“我画画的重点,并不是介绍西藏,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基本意识,于是产生了创作《第一声雷》的动机。 这隆隆的第一声雷,唤起了人的觉醒,表现了人类精神升华的一瞬间。”
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胡项城艺术的起始点就是这种建构起人类共同体的基本意识,或者说象征性体系。正是由于这套体系的创造性运转,我们才得以超越智人,创建庞大的社会和国际。因此,对它的信心和这种基本意识的随时崩解成为胡项城思维的两极。
一方面,艺术家对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想象是坚定的,他无数次在作品中以不同角度切入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例如在展览中 的《试图爬出垃圾圈的维特鲁威人》,五个木质的环高8米至5米,用木架连接,上面装生产生活消费废弃品。三个8米至6米的维特鲁威人,木质材料的人像,从材料上可联想到达芬奇时代的木质机械。废弃品是近现代工业后社会的排泄物。维特鲁威人和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同身受,这是艺术家唤起的毋庸置疑的心灵感应。
但另一方面,它们在试图爬出的一片史诗级别的灾难,不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工业化后果?而我们,也正是维特鲁威人的后代,与15世纪的启蒙相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文主义者。是我们自身把自己带到了不可持续的荒原。
在对垃圾艺术的处理中,非常有趣的是胡的象征手法。我们非常熟悉施维特斯的梅尔兹堡或是杜尚的尿壶,它们是由真正的物品或垃圾构成的。但在胡项城的作品中,垃圾往往是一种象征物,它常常并未真实出现。例如在《眼前的远方》系列中,银翼飞机和企鹅都是三维的实体,但垃圾却是它们背后的碎片化背景。这种实体与象征之间的对比形成了强有力的象征性,我们很难界定究竟是想象中的垃圾充斥了生活世界,还是垃圾已经被收录在我们有关未来的图景中,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世界,正是由我们的共同想象所界定。再换句话说,求仁得仁。你想象战争,于是就有了战争;你想象垃圾,于是垃圾便围城。这就是我们的全球化,它将遥远的想象强行注入了现实。
《环球箭头计划》更像是巨大的图腾,它所崇拜和恐惧的,是人类琐屑行为的力量。竖20米高10米宽14米长铁架,上面装有发光箭头以及发光水桶,另外有玻璃镜子、砖、木制的三枚剪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微不足道,但累积起来的能量,却如一簇利箭般让地球千疮百孔。
我们很少看到在胡这一代的人中,拥有如此蓬勃的创作激情和宏大渺远的历史意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战后遗产的继承上,胡与他的达达主义前辈站在一个水平的位置,但他从几个维度上深地切入了问题的核心。
《恐龙皮》是特别让人关注的作品之一,它无疑比《统领者的对话》显得更为简洁,因而更具沉思力,更加凝重。恐龙皮由生铁铸成,印有凹凸的各种证件文字。这些证件是人一生的各种重要证件。胡项城写道:“恐龙曾是这个星球上的绝对霸主,但在沧海桑田的自然剧变中灭绝。人类文明进入现代阶段后的加速度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但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何遏止因短视和自⼤而导致的自毁,是当代人无法逃避的问题。”
当胡项城将自然史与文明史放在同一角度去思考时,他已经远远超越了贫穷艺术的最初界限。巨大的历史被压缩在面前的生铁所象征的观念中,整个历史,既是真实的,同时也是人类虚无的建构,它终有一天会轰然倒下。历史,随着有厚度的恐龙的倒下而坍缩直至压扁。这件简洁的作品竟有如此丰富的意味,倒下的岂是一条恐龙,它简直是一次共同体倒塌的预演,或残迹。我们在它面前应凭吊谁?哀思谁?观想谁?不正如吉本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废墟上对古罗马帝国的幽思吗?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胡项城要重构的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人间日常。
胡项城的作品,深思悠远,构想宏大,体积宽广。他对生活世界的问题也并没有作任何美化和纹饰,而是每一次都在急进中揭示出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他的作品并不甜,也毫无意愿取悦观众,倒不如说就像一声惊雷,非要把你吵醒不可,或者就让你身处废墟,让你觉得生活与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取代》是他在2006年年上海青浦废弃的水泥厂制作的大型装置,由体量巨大的水泥、木、铁构成。一把巨大的水泥手枪捣毁了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但如今它已空心化,几千年农牧时代废弃的建材家具躺在水泥枪里呻吟。是生产力的你死我活吗?难道无法将它们和谐的编织在共同体中?
《不明构造》更是直接跨越到哲学层面的沉思,钢铁结构割裂了天空,在巨大的铁锈带下观众不明所以,灵魂出窍。艺术家思考视觉、心智和理性的界限形状,从这件作品开始,胡项城已经介入了康德与胡塞尔的领域。
惶恐惊疑是通向精神洗礼的必由之路,这恐怕正是胡的诗学——恐怖与怜悯,在一出又一出他所打造的装置剧场中,一个生活世界的蓝图被强有力地编织起来。艺术家带着雄心和豪迈,在《无限风光观景台》中,这种勇猛的心境一发不可收拾。他写道:“废墟都曾辉煌过。人的力量在涌动,自然物理力量在涌动,夜幕降临回光返照,沧海桑田,海市蜃楼风光无限。”从硕大的水泥孔中望去,似乎天下尽收眼底。它的圆形壁垒那么隔绝,但又那么无限。巨大水泥管道压在废墟上假设观景台,是对造化弄人的无常世界的无奈叹息,更是对屡毁屡建乌托邦的人类精神的赞美。
从80年代开始的《一声惊雷》,到青浦小西门传统建筑群重建,2010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艺术总监,胡一直长期旅居西藏、在日本和非洲从事艺术创作。现今他居住与工作在中国上海,他的作品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前,我们称之为85’新潮时期。胡项城的创作和85’新潮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又疏远的关系。他的铜雕和装置携带者85’新潮的观念艺术基因,但却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全球化气质。在非常早的时刻,他已经开始在作品中思考和呈现人类生活世界的命运及其能量。
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之为现象学时期,从1990-2005年,这是胡广泛涉猎民俗学, 非洲和日本艺术的时期,这对他2007年后的创作井喷起到了深厚的积累作用。 以《不明构造》为界限,胡项城的艺术从抽象的现象学思考转入现实,并迸发出更强大的创造力。第三个阶段是2006年以后至今,本次展览的大部分作品出自于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艺术家一扫贫穷艺术、观念艺术和装置的种种窠臼,而是专注于表达他所建构的破碎中的宏大,这种宏大的境界,比贫穷艺术更辽阔,比达达更振奋,比解构主义更严肃。
需要提醒的是,在今天香水四溅、霓虹闪耀、挡道的装置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艺术环境中时,胡仍然在用一种默默的悲观主义态度提醒存在的问题:我们的价值,我们所谓的存在的光辉可能“一钱不值”!这一点,与当代艺术领域里盲目的乐观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对他光怪陆离的作品不屑一顾,也可以嘲笑他荒芜渺远的重构努力,甚至许多年青艺术家早已卷入更为商业和甜腻的俗套中去。在碎片化和娱乐至死的年代,或许我们早已经丧失了廉颇式的精神孤勇。但我们不应忘记贡布里希的箴言——艺术家呕心沥血,我们至少应当了解他们何以至此。我想以这位已经颇有人生阅历的艺术家的一段肺腑之言结束本文:
“现代社会,科技力量确实为人类摆脱肉体生存的痛苦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享受着便捷舒适,却为由此带来的不可持续而心惊肉跳,为子孙后代的末来内心充满负罪感。我们从贫穷年代走过的人,深知极瑞贫困对人的摧毁力,因此对地球各角落赤贫的人们追求富裕是完全了解…在这进步与退步並存,希望与毁灭之间能否找到平衡这是问题的关键!”
Related Artists: HU XIANGCHENG 胡项城
Related Exhib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