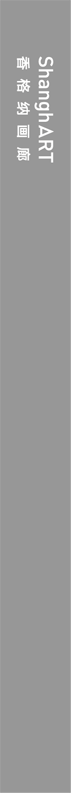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1-03 11:23
1997年出生于成都,毕业于Pratt Institute室内设计专业,现作为独立艺术家和空间设计师工作和生活于成都。
于2020年起系统性创作的系列绘画与装置保存了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联觉感受——一种因个体而异的感官混合现象。此系列中的联觉体验意在记录个体对于熟悉的周遭环境的陌生的体会方式和感官边界的消解。
RED: 鲁钰
公众号:蓝环章鱼
侯钰瑶,以下简称 H
鲁钰,以下简称 L
访谈内容同步更新知乎专栏:The MPI 对话艺术
H:最开始是如何留意到自己多感官间感知的互通能力,又如何将其开始进行记录或者形成作品呈现的?
L:联觉感受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不过那时不能算“留意到”,也不曾记录,只是自然地使用着这样的感官,也并不对此感到稀奇或惊讶。
开始有意识是七岁时第一次与家人买牛角面包。我想象中的牛角面包来源于别人念出它名字时的发音,这四个音节拥有的韧性、拉扯质感和粘性让我对这种烘焙品无比期待,然而见到空心又软的实物却感到大失所望,联觉的质感和画面与实际的物相距甚远,这种受骗感,让我对此印象深刻。
真正开始理解自己的联感能力、并进行记录是在2015年准备申请大学的作品集时,创作了一系列联觉的绘画和小型装置,随后断断续续持续至今。
图片
牛角面包手绘图
图片
「滚水的气味与声响」/ 2020
“闷声撞击
每一次击打不断笨重地弹跳
最终回归到同一个平面上
朝上同一方向直立
环境很暗
沟纹里或许藏污纳垢”
H:听觉、视觉以及触觉之间是如何传递的,是可以逆向的吗?比如手稿基本是从声音或者身体的触感上产生视觉,一些文字记录中对于气味的描述又回归到触感和视觉形态,假如出发点是视觉观察,会触发其他的感受吗?
L:视觉是可以引发其他感官的,但我不称之为“逆向过程”。在目前为止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中,其他感官都由视觉通道输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表达媒介的限制。如果借用其他形式的媒介和技术支持,嗅觉、味觉等感知的确也可以用于输出视觉,我也希望在之后进行这方面的材料和媒介研究,打破目前以视觉作为唯一输出的限制。
图片
图片
「青花椒」,青花椒的气味和味道 / 2022
H:通过自身感官观察外界,并由感官间的转化使之再现,在这个过程是完全顺应感受的自然发展,还是会在某些特定作品中加入主观的想法的干预?
L:感官间传递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就像碰到倒满开水的杯子会觉得烫。但联觉感受的发生、它的具体形态、感官转化的发展走向、强烈程度、或者说是哪一种特定感知,都绝对主观,但脱离掌控。而转化成视觉的过程更像是一种观察记录,就像临摹石膏像,我的记录工作就是尽力画得像而已。重现转瞬即逝的感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般会在作品的题材上选择可以被重复感受的体验,比如日常生活的片段,这样“石膏像”将一直置于可观察的范围内,我能用足够的时间去“画下”每一个细节。我也会筛选较好在纸上或空间上进行表现的作品雏形,这应该是目前存在的主观干预了。
图片
图片
「抽油烟机运行的声音」/ 2021 - 2022
H:在你的视觉化感知中,视觉的图像和本身生产声音的物件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规律的必然联系,形态上会有相似性吗?在一些装置中将产生源和自己的感受放置在了一起,比如「微波炉运行的声音」,相比于手稿似乎是在特别设置下为观众提供了一些去靠近作品的指引。
L:我有尝试过归纳规律,也发现过一些可总结的感官元素,比如关于“冷”的感受会以塑料质感的多边形框出现,而不同电器之间的声音在拥有相似性的基础上各有变化。
图片
「微波炉运行的声音」/ 2021 - 2022
这些联觉的可视化形态和相应物件之间并不直接关联。观众也以自己的方式从中间寻找到过不同的关联性,比如有人提到“揉塑料袋的声音看起来是单纯画出了揉皱的塑料袋”,但对我来说,我关注的只是那些絮状线条的动态和它们填充空间的方式。虽然这样的观者联想与我真实的感受过程不同,但我也鼓励观众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
其实所有的绘画都是为装置作品而画的手稿,或者说是简易施工图。在我的工作习惯里,如果没有前期大量的手绘和材料试验,施工搭建是无法顺利展开的。这或许是我的局限,但这样的方式令我安心。从另一方面,纸张有2D媒介的限制,而我的感受多是材质和建构方式,是拥有丰富质感的,装置更有能力去尽量还原我联觉中的质感,甚至是让人有机会真实触摸到我脑海中的感受。
图片
「保鲜袋被轻轻揉动的声音与触感」
「灶台打燃」「白胡椒」「蝉鸣」手稿
H:选择材料的时候,感知是再次转化的,材料的选择上同时考虑了直观的视觉关联和你自身特殊的对于材料的感知吗?
L:绘画和文字中表达的材料是根据感受到的质感和建构方式决定的,大部分在现实中没有具象对应。因此,确切来说,如果有足够的技术支持和精力,我应该开发新材料,而不是在既有材料中做妥协替代的选择。视觉上的关联是其次的,最优先考虑的是材质本身的性质是否符合感受。
图片
图片
「抽油烟机运行的声音」装置制作过程及局部
H:作品从声音的视觉化,到再多维的输出,而形成的装置又可以再次成为制造声音的物体,如果循环往复再产生声音回到新的画面,这个无限流动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子?
L: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能达到这样的无限流动其实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材质转移偏差的出现。如果理想状态下,材质完全符合我感受中的体验,两者毫无违和地仅与彼此关联,就会形成闭环,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实生活中能找到完全符合的材料非常困难,它们有时候拥有一些虚拟的、抽象的性质,比如“介于硬骨头和橡胶块之间的可形变粗糙颗粒”,那这时候在工作室可实施的条件内,可能会选择用表面裹着硅胶的石材,这样一来转译就出现了偏差,而你提到的“装置再生产声音回到新的画面”也就有了发生的机会。
图片
「设置手机闹钟时拖拽滚轮的震动」 / 2021
“介于骨头与橡胶之间的质感
撞击发出有弹性的回声
每一块间有斥力
松弛时总是保持着一条小隙
但也有引力
所以拉不太开”
H:有遇到过哪些反差比较大的感受吗?
L:我觉得铁锈的气味呈现的视觉就比这个气味本身更加令人愉悦。
人的声音也很有反差,不同的人的声音都在一个类似的基础底形上各有发展。人声听起来并不特别难受,但材质上它往往是一条纵向纤维丰富且僵硬的海绵,外周绒毛生长,间隙中填满粘液,每个人的黏稠度和间隙形态不尽相同,运动起来的时候纤维受到不同方向拉扯。
图片
「锈蚀金属的气味」
H:对于日常事物和常见场景的选择,也引起的许多观众的回应,而且发现很多人会对于同感有比较模糊的感受,但在看到你的作品后让这些模糊的感受变得可触碰或具体化,这让我想到通感力是否是可培养的。和比较多参与你的作品的人之间有过哪些讨论和意外的发现?
L:我也不能确定通感或联觉力是否可以被培养,但我想起来小时候与小朋友们交流联觉的经历。那时候也偶尔会对同龄人说一些类似“我觉得2是黄色的”或者“鸟这个字黏黏的”之类的话,大家也会很正常地回复我说“2不是黄色是蓝色”诸如此类。现在想起来可能大家小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通感,或者单纯地只是有强烈的参与话题和发表看法的欲望。
图片
图片
「木菜板上切块根茎类蔬菜的声音」 / 2020
“牙釉质质感,不过触感是更加磨砂的
略低于体温的温度,干燥的表面
一片一片地被无弹性的丝线缠起
有时有五边形或三角形的
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四边形”
在对作品的评论中,我发现几种很有意思的留言:
有一些观众对我的联觉表达表示高度赞同,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支持令我感到感激,也会有疑惑。因为所有的表达都是主观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不具有强的公共性,但大家赞同的反馈是否说明了联觉是可以被系统研究、被归纳、甚至是被准确翻译的?主观的体验也可能是集体的体验吗?
图片
「半旧的珊瑚绒毯子的手感」/ 2020
“粉尘滞结成的疏松的皱褶
越是小心轻触
越是黏化融解不成样子
反而是用力些
撕出的碎片倒还算完整”
有一种是认为自己并无联觉的能力,对画面没有感受,于是觉得自己“只是凡人”。这样的留言让我感到惭愧,我认为感受不到或有其他不同的感受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不能说明感受不到的人迟钝,也不代表有联觉的人更优越,只是大家的体会方式不同。即使是联觉者,也会有不尽相同的体会方式,有人对数字和敏感,有人对色彩敏感。
也有一小部分质疑的声音,认为我是在糊弄大家。这也是正常的,我的确没有办法自证自己的体验,或者分享我的躯壳和灵魂。这个系列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个人的记录,我只需要对自己诚实。如果其他人从中有体会到乐趣,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图片
图片
「黑胡椒」,黑胡椒的气味和味道 / 2021 - 2022
H:目前更多是关于观察与记录,会不会将这种能力发展成为一种媒介,而去做进一步的,可能渐渐剥离与现实产生的关联的创作?
L:这个系列的创作初衷就是观察与纪录,可以说是刻意地记录。因为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在逐年减退,于是想通过持续创作来使自己的感受能力保持敏感,或至少是在消失之前把感受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联觉的感受必须基于我的个体经验才可以产生的,如果发展到脱离现实的创作,我想应该是困难、且与初衷不符的。
2023.4
Related Artists: LU YU 鲁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