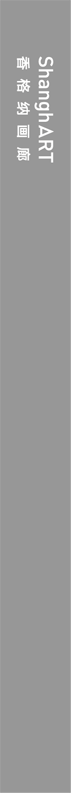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2-04 15:19
自十八世纪开始,欧洲的浪漫主义者渐渐将废墟视作一种理想的美学形象,作为一种往昔与现今的浓缩物、既存与不存的结合体,废墟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仅仅从当下这一短暂的“瞬间”中,人们便能捕获全部的“时间之流”。
在今天的汉语中,人们用废墟来描述业已消亡的建筑,而在过去,先秦的古人则将往昔建筑荡然无存后,留下的空间概括为“丘”。在近期开幕的展览“给未来的证物”中,策展人朱朱将北丘当代美术馆的展厅布置成了一个连贯、完整,因而也显得有些空荡、幽暗的“洞穴”,这座由南京北极阁丘陵内部的防空洞改造而来,以“丘”为名的美术馆,由此成为了一座具有历史感的“人造废墟”。在这个“洞穴”样式的展厅空间中,朱朱错落地安排了李怒与高磊两位艺术家近年的重要作品以及本次展览的委任创作。绘画、影像、装置等多种媒介的作品,以一种对话的形式不断探索时间、语言和知觉的多种命题,与作为“废墟”的美术馆相互内化,从外在表象转向主观情感,激发观众对空间的记忆和领悟。
进入展厅,迎面的作品《但愿上天让人理解并感受到自己的和他人的愿望》(Warm/September) 便释放着李怒对语言实验的兴趣。艺术家将镍铬合金线缠绕在玻璃灯管上,经由电流加热,在黑暗中间歇性地发出红光,“Warm”(温暖)一词悬空显现,而因为艺术家对英文连笔的刻意打断,我们又可以将此读为“War”(战争),置于最后的字母“m”代表的“人”(man),即成为了不同现实的抉择者。与这件作品在李怒2022年今日美术馆的“流沙即磐石”展览中的布置不同,朱朱并未将灯管设置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相反,他让空间上方天光与作品相互作用,使作品在未加热状态下也隐约显露出轮廓,并在美术馆的水泥斜顶上投射出类似书法的阴影。旁边的另一件霓虹灯管制成的作品《重复》,则以单词“Repeat”象征着历史、战争与现实的重复性。李怒在作品介绍中写道:“在周而复始的命运轮回中,我们盘旋着上升,或者下坠。我们在文明之中。我们在文明之外。我们在幸福之中。我们在幸福之外。”
与李怒带有某种诗意的发问、提示相比,高磊的作品更像是冷酷的寓言。高磊善于将“物质”这一语言的能指和所指进行组装和拼接。向外,回应李怒的作品以及作品外更大的世界,向内,则实现着纯粹物质化的对话。他的现成品装置由不同物件组合拼装,观众可以将作品区分为一个一个的单一物件,进行直接的解读,但也可以将之视作统一体,让物与物的含义生发多种隐喻。
在展厅二层,策展人朱朱将两位艺术家基于工作室拆迁经验创作的作品放置在一起,在一个共通的主题中,两位艺术家显示出了方式、方法上的迥异。李怒的影像《贝加尔湖》记录了自己返回已被拆毁的工作室旧址的经历。艺术家在衰败的废墟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处蓝色的地面——是曾经工作室厨房里的一些蓝色瓷砖,在周围的一切大多改变或消失的现在,这些地砖成为艺术家了重返过往生活的物理、情感锚点。而高磊以代号命名的装置作品《L-01》《R-01》,将高饱和度、强对比色彩的宜家桌面和插座、水龙头、棍棒、皮草衣领等现成物装置在一起,以“暴力”拼接回应在北方寒冬经历的现实逼迫。
李怒的作品《世界》,名称来自拉丁语中的“Mundus” (世界) 一词。这件由象征纯洁的汉白玉制成的作品不断暗示着人体肚脐的种种奇特概念——肚脐不仅是维特鲁威、达芬奇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所诠释的身体中心,还是罗马文化中城市和宇宙联系的隐喻中心。贯穿在罗马人建立“Mundus”的做法和李怒肚脐雕塑的蚀刻凹槽间的,是有关“挖掘”的概念——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城市的建立;也是隐喻意义上的:挖掘更深层次的真理和见解。这种向下的挖掘与当代社会强调横向扩张和向外探索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挖掘”,李怒呼吁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内省,一种要求我们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进行人性与未来之间关系的内省。
李怒在欧洲的学习和旅行经历,不仅激发了他对地缘政治、边境身份、异质性等话题的长期兴趣,也为他重新审视本土话题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系;高磊则惯于挑战先入为主的形式和表现观念,并时常模糊抽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李怒对生命的理解基于生命的现实权利,基于生命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存在;高磊则更集中于讨论一种永恒的、超越时空的生命观。
展览中两件体量最大的作品同样出自对“生命”和“神性”的诘问。李怒的《直到海洋被关进栅栏》以法国中世纪雕塑家菲利普·波特的墓室雕塑为原型,在原作外观——八个修士围绕一个贵族的身体排列——的基础上,艺术家变更了雕塑原本的材质和色彩,并引入动力装置。原作中的大理石和镶金被换为廉价的现代材料石膏和钢材,哭悼者的黑袍被替为白色,作为贵族象征的家徽也被移除,原本肃穆的雕塑不时传出激烈的拍打声响。作品带有显而易见的去神圣化意味,但同时,也借助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产品,视听化了今天社会中仍旧存在的,权力结构的失控。
高磊的《屏风-玛拿西之锯》与《直到海洋被关进栅栏》构建了一种复杂的对话。《屏风-玛拿西之锯》灵感来源于圣经故事,先知以赛亚在预言耶稣诞生的同时,因预言了不利于玛拿西王的未来而被锯杀。原作中那个充满暴力和痛苦的古代故事,被艺术家重新构想并编制进了现代工业式的刀模制造流程中,并以祭坛画与象征权力和王权的屏风形式再现了令以赛亚殉难的刑具。
在李怒和高磊的作品中,对“当下”的知觉构成了“给未来的证物”的主要部分,不过,所谓的“当下”并不意味着它是全新的,相反,它往往由更早的“当下”,已经不被人们视为当下的“当下”累积而成——这既是当下的起源,也是当下的结局——在两位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一系列对“怀旧”和“集体记忆”的关注。对于艺术家来说,集体记忆似乎是一个恒久命题,它的诞生也许源于个体对急剧变化社会的不适应,表象世界的紊乱和动荡,还有精神秩序的解体。
展馆的隧道空间作为此次展览的结尾展示了高磊的委任创作。山体的下半截成为隧道空间的背景墙,而潮湿的泥土味也仿佛成为作品展示的助力手段。高磊的“他山”系列被吊挂在空中,以最原始的状态被手电筒式的灯光照亮,作品通过模仿哥特式玻璃彩窗中的圣像框架结构,将日常物品转化为具有强烈仪式感和象征意义的图像。
向高磊的立体观视镜(《铁尾 双月 大树&黑钻》,2024)与被拉长的“洞穴隧道”望去,展览来到了末尾,观众似乎能感到,李怒和高磊两位风格不尽相同的艺术家,通过共同的对物质以及当下与未来的感知力,为惰性材料注入生命,在策展人朱朱设置出的多种情感、故事和概念的场景中实现了对话的可能。美术馆保留的防空洞的原始结构和历史感,以及其与周边山体的融合,让展览本身成为了一件时间胶囊,装载着现实的见证和追问。
Related Artists: GAO LEI 高磊
Related Exhib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