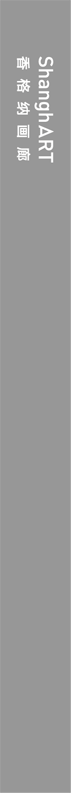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5-15 10:21
文/刘林
在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特别驻留项目“鸣沙”的现场,艺术家杨振中对一件旧作进行了升级。2006年,在上海艺术家自发组织的“38个个展”中,杨振中首次呈现了这件最初名为“我有一个梦”的声音互动装置:利用电脑变声软件的简单处理,观众在艺术家设置的演讲台上发出的声音会被转化为其它音色。在“鸣沙”项目中,这件作品的标题被改为“回响”(亦名“沉默即同意”):艺术家使用AI技术,将观众的声音转化为十个采样于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真人音源,从而实现台上一人发言,台下异口同声的效果。
1
位于上海杨浦区的敦煌当代美术馆,集合了两对极具反差的矛盾。首先是“敦煌-当代”,“‘敦煌’是几乎已经固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而‘当代’则处在动态过程中”,“鸣沙”项目的策展人陶寒辰这样说道;其次是“敦煌-上海”,这两个城市似乎也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深处亚洲内陆腹地,一个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而且乍看起来简直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两个极点。到底要如何才能让观众踏入位于上海的敦煌当代美术馆时不至于迷茫,正是“鸣沙”项目试图在美术馆开馆展“境象敦煌”之外向大家补充说明的缘由之一。陶寒辰表示,“邀请上海本地当代艺术家去敦煌驻留,再形成作品,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加接近敦煌本身的面貌”。敦煌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文化瑰宝,却也潜在地成为众人不得不背负的文化“包袱”,如果是怀着朝圣的心态进行这场驻留,或许我们现在看到的“鸣沙”项目就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因此,由曾经在2003年的作品《轻而易举》中“玩弄”上海的杨振中来“写生”敦煌就显得十分贴切,因为他的“包袱”本就不重。杨振中说:“我还是关注当下的状态,敦煌整个城市的生产已经和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乃至现代工业文明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靠旅游支撑起的状态。”
2
“鸣沙”项目的核心作品是艺术家拍摄敦煌著名景点鸣沙山的同名影像《鸣沙》(2024)。即使你没有亲自造访过鸣沙山,想必也曾经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鸣沙山上人满为患的热闹场面。正像陶寒辰所说,“手机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失的电子器官”,短视频时代中的“传统”或许比当代艺术还要更加当代。艺术家将镜头对准这种当代,采用纪实手法记录那些不畏寒暑只为出片的游客,并以卷轴画逐渐展开的方式平行展示敦煌石窟壁画中各类神佛形像,后者是游客和旅拍摄影师们致力模仿的对象。但是,我们很难说这种模仿是拙劣的。随着短视频的传播,某个特定角度、姿态和时刻的敦煌,将比那些即使你花费高昂费用也仅能在一个非指定性的、缺乏照明的环境中短暂停留一刻钟的“特窟”里秘不示人的(甚至连高清电子图像资源都已经成为垄断性的)经典菩萨、飞天、力士、舞伎形象要鲜活得多。
3
“古代遗物究竟是否丰富, 我仍不敢臆断。等到系统的发掘开始以后, 露出一层一层的木牍, 同各种废物混杂一起。随即看出这是多年以来积聚而成的一个古代垃圾堆……”沉迷于历史之人,往往试图在“古代垃圾堆”中寻找意义。鸣沙山在旺季(每年6-8月)日均游客接待量近6-7万人,每当日落月牙泉,白天cosplay的游客就转入“万人星空演唱会”模式,届时会有一位领唱带着漫山遍野的歌友齐唱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直到深夜一两点钟,人潮才会慢慢退去。在观看日出的人群上山之前,鸣沙山景区保洁队需要快速出动,清除歌迷们留在大漠里的各类生活垃圾,以免给后世考古学家增添烦恼。
4
杨振中长期关注“劳动”议题。2003年,他与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员工合作,完成《春天的故事》。在这件作品中,1500名员工以流水线的方式朗诵出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的《南巡讲话》。如果说在2003年全球化早期的流水线中还能看到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伪装》(2015)中已遭全然异化的劳动者只剩下近乎麻木的专业性与标准化(影片中所有人都带上了由自身面容3D打印的面具)。2020年,在“现形”系列中,艺术家在影像作品《清凉》中记录了福建崇武石匠为其制作装置作品的过程。在前往敦煌驻留之前,杨振中便对敦煌中的“劳动”因素,特别是为各类出资建窟供养人绘制洞窟壁画的本地匠人抱有兴趣。从另一个角度看,《鸣沙》中的旅拍摄影师与游客,与古代匠人与信众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的同构的:他们都是有服务对象的“图像生产者”。
5
从2020年的“现形”系列开始,杨振中便将其对于“劳动”主题的关注集中在“工具”这一概念上。在“现形”系列装置作品中,锁链形态的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工具》(2024)中,这一点得以延续。在“鸣沙”项目现场,54组由锁链连接的各类手工劳动器具——由艺术家收购于敦煌当地农村和二手闲置网站,通过“一体化3D雕刻技术和经来自浙江东阳工匠的手工打磨,这些曾经作为劳动阶层及其所处生产关系中所留下的痕迹旧物,被赋予新的想象空间和美学意义。”在“现形”系列中被束缚、扭曲、摧残的石头(人类最初学会使用的工具)显得更加锐利难当。劳动工具同时也是武器。“在中国历史中,民间械斗使用的兵器无非就是锄头、镰刀和榔头。”艺术家如是说。用以将中国人“钉死在土地上”的工具,随时有可能成为挣脱枷锁的利器。就像在算法制造的图像海洋中迷失的民意,往往也会在抵达一种极限后发生某种质变。
6
敦煌的“全球化”是贯穿古今的。在敦煌驻留期间,艺术家和策展人去了趟敦煌光电产业园的“超级镜子发电站”。这个项目的全名是“敦煌首航节能100兆瓦熔盐塔式光人发电站”,是一个由12000多面定日镜(单面镜子面积为115平方米,由35片子镜面组成)组成的面积近8平方公里(澳门面积的约四分之一)的超级工程,通过镜面反射,高达260米的吸热塔在荒漠中发出如太阳般的刺目光芒,即使在数十公里以外依然清晰可见。敦煌是中国日照时长最多的地区之一,全年高达近3500个小时(顺便一提,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与雕塑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保存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敦煌年均不足50毫米的降雨量和高达约2400毫米的蒸发量)。每当鸣沙山景区挤满红男绿女时,超级镜子发电站也进入了它的旺季,其夏季最高发电量为227万千瓦时。
7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敦煌莫高窟的雨量出现了缓慢增长的趋势。空气湿度的增加会驱动莫高窟岩体盐分向壁画地仗层迁移,从而导致壁画表面在溶解与结晶两种状态之间反复,最终导致“稣碱”病害,后者对于壁画的破坏性的不可逆的。”说话声音大一点,起甲的壁画可能就掉落了”,一位敦煌壁画修复专家曾这样说道。
8
你有没有试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些重视作品完整度的艺术家(无论古今)是否愿意他人在早已破败的作品现状前驻足凝视?那些期待通过作品永生的艺术,首先要想方设法延长其作品的生命,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9
在“敦煌-当代”的奇妙组合之下,“鸣沙”项目中乍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三组作品——《鸣沙》《回响》《工具》——之间产生了复杂相关。诸如平台资本主义同质化生产与个体创造性(能动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日渐式微的宗教信仰与当代“神迹”之间镜映关系、当代文化创造与传统文化底蕴之间的互相定义以及气候危机背景下“人”与(文)“物”之间的尴尬关系等等,都让三件作品最终成为一个整体。
10
拍摄《鸣沙》期间,因为风沙过大,杨振中的摄像机镜头进了灰。等到他为此寻找当地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咨询时,对方称自己已经离开敦煌。旅游季一过,大家就开启休假模式了。那些临时被雇来的摄影师也像鸣沙山上的流沙一样,向文旅风向所至之处移动。“这里夏天最热闹,秋天之后大家就去三亚了。要么云南,在那里他们可以把你打扮成傣族……”
Related Artists: YANG ZHENZHONG 杨振中
Related Exhib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