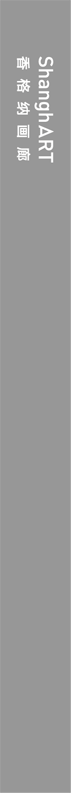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6-16 17:02
7月25日,在张文心《次表面湿生》展览开幕现场(点击划线处查看展览现场推文),艺术家邀请了她的两个好朋友进行了一次有关展览主题的对谈。现在,我们将对谈内容以纯文字的形式完整地呈现出来,全文7000多字,希望你能拥有不被图像打扰的、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对谈嘉宾
张文心
陈 旻
芬 雷
郭 熙
郭熙 欢迎大家来到想象力学实验室,参加张文心个人项目《次表面湿生》的开幕活动。这个项目我们跟张文心共同工作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中间经历了多次方案和主题的讨论。今天我们邀请芬雷和陈旻在这里做一个对谈。陈旻是策展人、艺术家和译者,中国美术学院的在读博士,2019年获得Hyundai Blue Prize策展人大奖。芬雷是艺术与出版策划人。我们先请张文心讲几句。
张文心 谢谢大家今天来。这个展览是我跟想象力学合作这一年来,经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加上媒介和材料方面的实验,进行的一个实验式呈现。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项目的背景资料,可以去想象力学公众号看我在上面发的四篇主题文章。(链接见文末)《次表面湿生》这个展览的概念有两个东西拼成,一个是“次表面”,一个是“湿生”。“次表面”是一个虚拟建模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渲染材料的方式——光线在一个表面穿透,还没有达到另一个表面的时候,在两个表面之间不停反射,产生的一种类似内发光,像玉石或皮肤一样的视觉体验。“湿生”是一个佛教概念,它指的是有情众生的一种生命形态。我把这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描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既是反映我自己目前在杭州的一个生存和创作的状态,也是对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不管是后媒介时代,还是渐渐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二元的世界的反思和一个开放性的讨论。前两天我跟芬雷还有陈旻都有一些讨论。想先请芬雷来说一说湿生的概念,我们讨论过跟佛学有关的问题。
芬雷 佛经里讲 “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指有情众生的四种生命形态。《楞严经》里说的比较清楚,“胎因情有,卵唯想生,湿以合感,化以离应”。胎卵湿化,情想合离,说的是不同的情执。佛经里说的“湿以合感”,其实是在解释一种颠倒乱想的发生方式。其中的“合”主要是覆盖、笼罩的意思,也有聚合、联合的意思。湿生的生命形态以及情执状态,很难和依附的环境分开,河水里的、沼泽里的、湿土里的,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情境关联在一起。佛家常说,十方湛寂,本无方所,但有情众生往往各有执着,所以有四生、十生、十二类生之说,分解妄想,解脱业力。“次表面湿生”是融合创造的概念,前面文心也说,来自3D的渲染处理,这里“湿生”的指向显然与佛经的旨趣不同,因为佛说毕竟空,而次表面是说透光材质的色感——虽然是虚拟的。简单来理解“次表面湿生”,可以是对湿生状态的次表面处理,或者是基于次表面的合感发明,而且艺术家的个人记忆、旅行中的神圣体验、杭州湿生环境的取景等也参与了进来。这是一个相生相灭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聚合、联合的过程。“湿以合感”这部分,我想可以待会再说,这里是可以引申到一个不那么佛系的地带去的。然后,文心可以再介绍一下展览,因为我比大家了解得多些,看的偏,转的也快,所以一谈就有点远,很容易跑题。
张文心 既然说到这里,我想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展览除了中间房间的幻灯片之外,都是我近期创作的作品。幻灯片是我四五年前创作的一个系列《瀑布招待所》,它像是一种离开后的回看。这四个房间可以被看作四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以不同媒介的作品呈现。第一个房间有点像我在山里行走的时的发现:我在池子里看到动物产卵,看到太阳变成月亮,在树林中迷路……是这样一种探索感受的外化呈现。第二个房间是我结合了“湿生”的概念,再现了生命如何通过模仿环境去生成的过程,我把在室外雨天时拍摄的照片进行了镜像的处理,人眼会自然地把对称的图形辨认成有生命的物体,或者是辨认出脸一般的相,这些都是我拍摄的没有生命的一个宏观环境,一旦进行镜像对称它们就变成了微观的、神秘的。第三个房间有点记忆宫殿的感觉,你可以夹在两扇门之间,让自己产生一种类似被催眠的感受。后面的展台则有点借用考古学中底层学的概念。我们的土地是不同时空叠加的状态,但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去给事物下定义的时候,却往往要把某一个事物的意义固定和强化。我们总是非常容易就借用到二元论的观念,或是人类/非人的区分,我希望可以借用地层学的工作方法去把这些连接起来,可以不再用非黑即白的判断方式。第四个房间是我想象出来的一种湿生生物,它有点像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状态,即介于人和非人之间、动物和数字之间、虚幻和真实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的大脑会习惯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中,似乎很害怕跳出来之后就会跌入一片虚空,但是我喜欢去创造这些比较奇怪的,看起来似乎有些攻击性或者有点恐怖的画面,这些画面让人有一种类似幻觉或者是迷狂的感受。我其实是想要做这样一个尝试:就算走出了舒适区,前面还是有一片广阔的地方,它可能很奇怪,但它并不会使你突然坠落,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之前跟陈旻聊到过,像我在这个展里面借用的很多湿生生物形象,它们是雌雄同体的,我们也可以去扩展开讨论一下基因技术、无性繁殖和赛博格等,以及人如何可以接受自己,接受他人,接受其他物种,成为综合这些东西的一个存在。
陈旻 我跟文心认识一年多以来,在日常沟通之外陆陆续续有过一些讨论,对她这两年的创作有作一个粗略的跟随,也看到了她对过往创作的重新思考。我跟她一样都是学摄影出身的,相对比较了解二维图像,却又觉得二维图像在今天似乎有一些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东西,所以文心转向了用三维图像的介入去建构一种虚拟世界,我转向了策展和写作。刚才文心提到了赛博格和二元对立,我前一段做的展览中也涉及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比如黑格尔的二元辩证、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身心分离、阴和阳、男和女、黑夜和白天……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形态是否真实存在于自然中?前几天我在浙江某段高速公路的公共休息区中已经看到无性别厕所的存在,这个年代 “去性别”的讨论似乎已经进入到了公共领域(当然在中国尚有很多阐释空地)。所以,如何去打破二元对立和非黑即白,都是我们当下工作中比较关键的问题。
关于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这里简单引入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位美国的女性研究者、女权主义者和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者,唐娜·哈拉维写出了《赛博格宣言》,这篇文章首先涉及了一种跨界研究。什么是赛博格?为什么哈拉维把赛博格和女性主义链接起来?最好懂的例子就是《攻壳机动队》——巴特是一种肉身和电子机械义肢的结合体,而草雉素子最终通过将记忆和意识上传,成为一个无肉身的意识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幻的想象,那就是一种去身体或者去性别的未来,不再需要依靠两性繁殖的方式去延续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女性主义的其中一个议题。之前芬雷谈到了哈拉维提出的“要亲缘不要婴儿”问题,这让我想到了想象力学实验室推送的张文心的第四篇文章(点击划线处查看推文)中提到的蚯蚓,这种雌雄同体、异体受精的动物。也就是说,蚯蚓同时具有两种性别,其交配方式非常复杂(让人想起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其次,某些高级蚯蚓可以重生,可以自体分裂,把它切断之后,不太重要的部位可以重新长出来。它可以向死而生,从一条蚯蚓变成两条拥有一模一样DNA的蚯蚓。这里我想把话题再抛回给张文心,请她讲讲,为什么在创作中用到蚯蚓这样一个动物的意象。
张文心 为什么使用“湿生”这个概念,其实也跟之前大家讨论的“低端人口”有关系。一般去网上骂人,最恶毒的话,可能就是把对方说成一条虫子或者是一条虫子的幼虫,这是最贬低人的一种骂人的方式,为什么?难道它们就是比人低等甚至不不配存在的生物?中国的农业文明在5000年之前就开始了人工育种,之所以土地可以出产很多粮食,蚯蚓是功不可没的,蚯蚓是是农人的朋友,而且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中,经常会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像父权社会中,男性一定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要有车有房,然后女性需要温良恭俭让,要顾家什么的,这些到底是谁规定的?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去尊崇这些规则,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条蚯蚓或者做一个虫子?是否虫子的身上已经没有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就像刚才陈旻提到的蚯蚓可以断肢后重生,它的生命力非常坚强的,而且它的存在让土壤更加疏松、更加适合植物的生长,其实它是在默默地做着非常伟大的事情。它并不是低贱的生物,它只是一种很基础的生物,它是属于和代表大地的。对照来看,现在马斯克在还有中国航天局等等都在追求登陆火星,似乎天空的崇高理性与光明才是更有意义的、更能发挥人类光辉的一种存在,但是,是否大地的幽暗、潮湿和生育力,已经不再被我们需要了?所以这个展览它很多的土地气息,以及土地中湿生生物的意象。当然女性主义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在远古人类的信仰中,大母神崇拜非常普遍,像是中国有女娲,西王母,古希腊有盖亚、丰收女神土地女神迪默特尔(Demeter)这样的一些女神的存在,还有像古埃及的伊西斯。在想象力学的赞助下,我去了一趟埃及调研,有一个东西很启发我。古埃及的神话中,太阳是从黑夜女神的体内出生的,每天晚上黑夜女神把太阳吞下去,第二天早上再把它生出来,光明从黑夜中诞生。所以天与地的关系并不是天是高的地是低的,它们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不管是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总之被各种主义所裹挟的——现代人的生活中,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更多的可能性,似乎一定要变成某一个或者某一种标准中的优越者,那么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追求优越?是不是优越和低下可以互换?所以在这个展览中我是比较想要去讨论这些问题。请芬雷老师补充。
芬雷 文心之前发在想象力学公众号上的几篇连载,推荐大家看完展览之后再去看一看。(链接见文末)在这几篇文本里,她有一个系统的梳理,也不能说系统吧,应该说,她试图去把很多事情都写进来。这里面有她个人的过往,她个人经验当中记忆的事情、家庭的事情,还有她自己的艺术经历,跟图像有关的,跟图像处理有关的,然后,值得留意的是,这个图像处理或者说图像构成,又进入了一种思辨的过程,类似自我技术一样,也是一种艺术转换。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点,大家在看展览的时候,通过这些图像可以去体会艺术家堆叠进来的、感知交错的内容,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记忆和经验融合进来。然后,艺术家还有神圣体验的一部分内容,神话也好,宗教也好,在我看来更加地是一种秘密仪式,属于个体生命的秘密仪式。关于这个秘密仪式,并不是说完全隐秘的,而是别人多多少少可以感知到的,但是你永远无法将其和盘托出。这是一个在你内心当中的秘密仪式,它会以某种形象或者某样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你生命经验中阶段性的、时间性的这么一个事件。借用佛经里说的,它可能是虚妄的、杂染的、执着的、变易的,它并不远离颠倒梦想。这是我补充的第二点,关于秘仪的部分。
第三点补充是关于文心和陈旻提到的赛博格。其实在我理解当中,赛博格的意思,对于“次表面湿生”这个展览来说,就是图像的处理、构成和制图参与了图像的表达,因此也传递并塑造了我们的感知。赛博格,其实跟“命令-控制-交流”有关系,是如此控制论意味下的关联所导致的一系列事件,还不直接地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赛博格风格化的那种东西,电影场景,服饰设计等。比方说,对图像的处理,通过次表面的材质渲染,这种方法看似只是一个工具操作或参数设置,但它确实也支持了感知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哈拉维“赛博格宣言”的意义上,感知的亲缘关系就这么被再生产出来了,有点意外中的反抗,也是再生意义上的重新联合。目前说的这些,都是在哈拉维强调的一个基础上,即,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到信息社会。一个东莞手机加工工厂的女工,和一个杭州的使用手机居家办公的公司女职员,把她们联合在一起的,除了苹果之外,还有信息,以及这些信息背后“命令-控制-交流”的赛博格情境。
但是,赛博格还是太概念化了,对于“次表面湿生”这个展览以及这个现场来说,并不必然需要这层解释。如果一个观众,既不了解赛博格,甚至不了解艺术家之前的工作,也没有读过想象力学公众号发布的连载文章,那么他/她可以如何观看这个展览呢。我想以一个了解的展览的人,再补充三条看展的线索(也是三个提问吧),同时也是对展览现场可能激发的感知状态做个揣测。
第一条线索是感知和边界。这些图像既吸引观看又排斥观看,那么当你去看的时候,会如何感受那些游荡在看见与看不见以及不可见之间的那种界限状态,在感知和边界的问题上会有哪些想法?第二条线索是图像和叠置。为什么一个艺术家要通过图像叠置的方式来呈现一个相或非相?在相与非相、相生相灭之间,一种生物或生命形态是如何被理解或被领会的?拟生也好,仿生也好,这里面似乎的确有一种模拟和转换。第三条线索是秘仪和痕迹。艺术家通过展览,营造一个像祭坛又像某种能量发射的这么一个秘仪的现场,然后在现场空间的4个地带展转发生,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个迁流的痕迹?这个痕迹,在那个仿若地质勘探或考古挖掘的工作台上,似乎有一个更直观的呈现。我补充这么多吧。
张文心 我回应一下,刚刚芬雷说得我很同意。我需要亲手掌握非常多的技术,在创作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安全,所以我自学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图像处理软件,基本上都能够达到可以就业的水平,但是在那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我可以专业的使用这些软件,那么我很容易把作品变得很美。一天可以产出20、30张可展出作品。于是,我就有了一段时间的迷茫期。在现今,作为一个所谓的当代艺术创作者,我需要去诉说什么呢?后来我到了一个关键点,即,我不希望去创作是完满的、闭合的、闭环的或确定的,我也不希望我的作品是在观众眼里是不用犹豫,不用去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就可以接受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开始接触时会造成观看者的抵触感、厌恶感甚至恐惧感,然后之后慢慢的可能会唤起观看者内心的某一些某个角落,某些曾经被压抑感受。我在写作时和在创作图像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在写作时候其实是追求逻辑,会引用很多文本,然后再把他们和我的个人经历进行相互映射,然后再寻找到某一个开口,让新的东西在其中生成。生成的结果也许是我完全没法预料的,在创作图像的创作时候,我会把自己放逐到某一个环境中,比如说我先制定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在雨天进行拍摄,或者只拍摄公交车的头站和底站——像是一个动作冒险RPG游戏的方法。我最害怕的是在文字和图像创作思维之间进行转换的时候。我没法平滑、舒适地进行转换,这个过程中总是先包涵着某种摧毁,再通过不断地穿透和反射,达到重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得以更了解我所使用的每一种技术和每一种媒介。就像次表面湿生生物那样,创作也是在不同的表面不同的领域之间不停的穿梭,不停地跳出已经熟悉的已经美丽的已经完美的已经光滑的已经可以去跟现在的讲究流量和讲究资本的社会完美对接的东西,走出来,进入一个荒蛮粗糙的领域,进行一种聚合/合成,创造一种看似有点恐怖和陌生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我创作激情的来源。之前我跟陈旻也聊过,类似这样在不同的媒介之中穿越创作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发散一下。
陈旻 其实到现在为止,在文心的创作当中先有图像还是先有文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谜。但是每次读到她的文字,都挺有画面感的。也许这种写作是用去图像化的方式去创作图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刚才听文心讲述她的创作,让我想到几件事情,在此抛砖引玉一下。首先是技术层面的,有关3D绘图软件,比如用unity或者C4D去创造图像,或者去创造世界。我们两个都是电子游戏玩家,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时渴望像游戏设计师一样,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在座可能有很多观众也是创作者,大家是否都有一种创世的欲望?也许 3d绘图软件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这种可能性。
其次,回到这次展览的标题,《次表面湿生》中的“次表面”是什么?这个词汇来源于3D软件的建模语汇,描述了人的表层皮肤下面的另外一个图层(layer),一种从皮肤的内部去发光的散射机制。如果说人类一直尝试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重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构成方式,那么3D软绘图件是否和人工智能和神经脑研究等前沿科学一样,试图去搭建一条模拟“真实”世界运行方式的通道(通道这个词同时也大量应用于绘图软件)?也许这种过程导向将决定最终生成的“真实”是什么样的。
最后,也是文心的创作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通路仪轨(rite of passage),一种去“达到”的秘密仪式。刚才她也谈到了两扇门当中的某个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和基督教的limbo,或是“次表面”是否都构成了某种仪式性的通道?当然迷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存在于很多民族和文化当中,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是《西部世界》当中的螺旋迷宫。同时,迷宫的意象和母胎的意象有一定重合性,有意思的是,螺旋形态是可以自如膨胀收缩的。卡夫卡曾经在《地洞/巢穴》中提到地下迷宫,带给人一种回到母胎的感觉。而到达迷宫中心之后,人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重生”。但是,重生这个结果是否重要?我觉得过程导向是文心非常重要的一条创作思路。虽然在古希腊神话中,忒休斯最后走出了迷宫,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文心,走出迷宫或走到迷宫中心这事情是否重要?
张文心 看每个人。通路仪轨是人类学中对某些古代仪式类型的表述,比如像成人礼、结婚礼或者是葬礼,它们使人的精神从一个阶段过度至另一个阶段。打个比方,你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一片混沌的空间,此时眼前还有一扇未打开的门,这就是仪式发生的时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排时间表时,把多个任务严丝合缝地填满表单,这其实就是越过了中间的过渡阶段,就像关上一扇门之后立刻踢开另一扇。这其实就形成了一种线性的,我们所说的,日常的生活状态。什么是非日常?就是你拉伸两扇门之间的时间,用仪式或者游戏,或是文学、创作、艺术、音乐、非惯常体验的方式把它延长,让变化在这段过程中产生。在戏剧理论中也有个概念叫做叫做阈限阶段(liminal stage),阈限阶段就是在两个场域之间的空隙的阶段,当人进入空隙之中,戏剧才得以产生,因为如果你不做停留,那么时间就只在日常中不断滚动。我在展览中其实也希望可以建构出这种过渡性的混沌时空,它在生成,又没有完全生成,你能看到一些,但是你不确定它是什么的一种状态,在观察它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去想象自己平时是否也偶遇过这样一个阶段,你是否给自己留出了这样的一种阈限阶段,让变化自发产生,去治疗自己或者是去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展览中,我对此做了很直白的呈现,比如,我使用了半透明的投影膜,当你走在中间时,就像走在一个旅馆走廊中——左边有一扇门,右边也有一扇门,人被夹在中间。,它会让人产生一种类似催眠的感觉,你似乎很安全,但又是游移不定的。对于黄色房间的照片,也是这样。比如,我拿到了一张照片,我可以把它拼成千万种不同的样式,但我会选择一个非常最暧昧的点,让“相”停止在那里,它并不指向明确的目的物。于是,每个人在图片中看到什么,是由自己心中所想决定的。也就是说,我提供一个场域,但过渡性仪式是由观看者自己来完成的。我希望观看者可以借用展览这个小窗口去观看阈限阶段的一种表现方式,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多给自己留一些窗口去生成一些元认知,也就是说去认知自己是如何认知的,去觉察自己的思维模式。由此,每个人也就可以成为创作者。
Related Artists: ZHANG WENXIN 张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