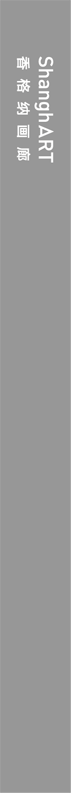2025-09-19 11:53
文/秦弘
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就像一艘在大海上飘荡的忒修斯之船。每当我们要从某种境况中挣脱,从某种窠臼中实现超越,似乎就要和“过去”作某种告别,以至于我们总是追求一种不断更迭的新我。在这种情况下,逝去的时日和生命经验往往会在被个体短暂“抛弃”后,却在未来的某些瞬间、契机和顿悟后重新被赋予价值,作为生命整体不可分割的价值。
周力个展“至近至远”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5
对于艺术家周力来说,她的创作正是其不断审思个体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关系,个体与他者的关系后的结果——不断变幻样貌又能在超时间性的线索中反复洄游,一种“共存共通,至近至远”(舒可文语)的状态。
周力,《线》,不锈钢,190(H)x 67 x 100cm,2018
由艺术批评家舒可文策展,正在香格纳北京举办的艺术家周力个展“至近至远”,在呈现其近年新作(包括在不同尺度和材质的碰撞之间构筑对话的三件雕塑作品)的同时,亦首次展出其创作草稿/小稿及相对早期的架上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窥艺术家标志性语言“起源”的路径。正如策展人所言,在大尺幅作品中,“色彩与线条被赋予了一种能量,似乎能打破画框的内外界限,弥漫四周内外相连。在丙烯等综合媒材的叠加中,铺展出通透、层叠的画面,各种元素展现着各自的勃勃生机,同时又彼此呼应,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静。”
周力,《玫瑰雕塑》,不锈钢、3D打印,30(H)x 8.5 x 7.5cm,2019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周力的作品中看到“张力与和谐的共生,轻盈与沉重、近与远、轻与重在这些作品中自由流动,经验与世界的共振,偶然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周力作品的基调。”这一切的发生,正是过去生命与此时此刻形成回响的复杂结果。
前:《2020-2025》之一,布面综合材料,180 x 180cm,2025
后:《夜:光之玫瑰》,布面综合材料,250 x 600cm,2023
01 时间之流中的“自画像”
从个展“格林迷踪”(2020)开始,周力的创作始终保持高强度,并且在每一次的更新中反复辨识个体自我与复数自我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始终需要追溯周力在其艺术生涯早期的“自画像”系列中的认知原点。发端于1988年的“自画像”系列创作,以及艺术家后来在考察陕西榆林石窟时邂逅的水月观音形象,在具象/抽象的边界显隐,有时化作依稀可辨的形象,有时又彻底抽象化为一根线条——艺术家的线条功夫得自其长期的书法实践,特别是对魏碑书法中笔画力度的提炼,再到环形、团块,以及以此为基点的雕塑/装置创作。
周力,《自画像》,汉白玉,45(H)x 20 x 20cm,2022
2024年在西藏拉萨吉本岗艺术中心的个展“四季”,成为艺术家对于“我”与“我们”领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至近至远”现场呈现的《西藏记忆:度母》(2024)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地的神秘之旅对于艺术家绘画作品中精神性因素的推进作用,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在背景中隐约看到一个近乎虚空的“人物”形象,不仅仅与吉本岗神殿遗址中几经剥蚀的画面中的线条、色彩与形象产生关联,同时亦形成艺术家再次造访过去-此刻-未来,以及我-非我-他我的契机。
周力,《西藏记忆:度母》,布面综合材料(丙烯、矿物颜料),240 x 190cm,2024
先于香格纳北京个展开幕的“一花一世界”,是周力在韩国的首次个展项目,上述“我”的状态集中地以“花”的形态示人。舒可文写道,花朵“形单影只又坚实,颜色沉重又姿态繁复,执着又自在。”在中国书画的观看哲学中,看花是花,看花不是花往往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境,甚至在可以被无限切分的时间中实现瞬间变化,一朵花的形态不会仅仅“通向抽象/具象的坐标,视看的感受和意识的方向是拆不开的。五味杂陈间的偶然动感和某种稳定力量,共存共通,至近至远。”
周力个展“至近至远”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5
四季流转,花开花落,生命在曼陀罗式的轮回构造中生生死死,我们看到了一种逐渐走向精神性、逐渐抽象化(这里的“抽象”并不是西方现代艺术意义上的“抽象”,而更近似于“山水”的境界)和自然(同样的,这里的“自然”并非西方“自然-社会”二分法下强行划分的领域,而是“自己而然”)化的自我形象。
02 “线”索
在《一花一世界:涅槃之一》(2025)中,不同色彩(心迹)区域的划分有了新的“线”索,一个若隐若现的九宫格成为肆意线条与色块背后起到稳定与平衡的关键。就像艺术家在谈及法度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时引用陆九渊,“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她认为这是一项非凡的精神成就。舒可文说,“理性的对立面从来不是感性,而是非理性;感性的对立面不是理性,而是麻木。”
周力,《一花一世界:涅槃之一》,布面综合材料,150 x 130cm,2025
正因如此,艺术家将自己辩证地置于“矛盾”之中,在《一花一世界:涅槃之一》中,红色如火焰般展开,反而映衬出底层的浅蓝色及其逐渐聚焦于空间内部的神秘光点,不同区域的划分使用了多种类型的线,有色相差异形成的虚线,有几乎融合的不稳定的边缘线,亦有笔直的,试图取消所谓“绘画性”的线条。尽管我们可以在艺术家的旧作《缠绵》(2015)中看到这些分隔手法的样貌,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在艺术家的整体艺术实践与生命体验不断变迁的若干瞬间中被构造的。
周力,《缠绵》,布面综合材料,250 x 600cm,2015
童中焘认为,“线条”本质上不切中国画,我们在谈论中国绘画中的“线描”因素时,实际是建立在西方“积点成线”——关于力度与运动的形式科学的基础上的。点、线、面是西方现代主义——发端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基于透视法的古典主义范式——空间观的基础,这种思维模式将线视为一种区别于点与面的中间状态,一条没有实存、但可以用以分割数理空间的边界。中国传统绘画强调的“一画”则是“线”的抽象与具象的结合,在周力绘画中,“线”与“非线”是没有差异的,线与“非线”同样可以起到标识对象轮廓、光感,乃至情绪、思想边界的作用。正如此前有论者指出,周力绘画中“线”形式的目的并不在于画面(视觉性意象)本身,而是在超越抽象/具象二元论的基础上表现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存在状态,这便是在跨时间性的视角审视周力创作的意义,重点不在于可见的形式变化本身,而在于不同形式背后一贯的结构性的、本体论的内容。
《一花一世界:涅槃之二》,布面综合材料,250 x 600cm,2025
03 创造性的轮回与演进
在藏地期间,艺术家首度使用矿物颜料,并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沉稳的饱满”。在愈加自由甚至张狂的笔触中,颜料以其接近原本物质形态的样貌实现了一种创造性的轮回。在“至近至远”现场,我们会看到艺术家在2024年使用藏纸和矿物颜料绘制的数张草图,因为矿物颜料自身的特性,无法均匀附着在绘画载体(藏纸的主要原料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海拔6500米以上生长的一种名为“瑞香狼毒”的灌木树皮,有趣的是,矿物颜料本身亦是制作藏纸的重要原料)之上,反而获得一种天然的“前现代”隽永,不禁让人想起在纳木错及阿里地区的原始岩画。
草图,藏纸、矿物颜料,50 × 75cm,2024左:草图,藏纸、矿物颜料,75 × 50cm,2024右:草图,藏纸、矿物颜料,75 × 50cm,2024
但当我们仔细观看艺术家早在2018年为创作大尺幅绘画准备的草稿中,虽然材料迥异,却能让人感知到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跨越时间性的关联。不一样的是,在2018年的旧作中,我们尽可以在艺术家的描绘对象中寻迹日后其大尺幅抽象图式的“出处”,在其中一幅看起来是在描绘天空的作品中,艺术家试图以线条捕捉无形可辨的风“迹”,而在描绘某个山坡的形象时,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线条之间并无二致,而且都居于轻与重之间,悬停在艺术家彼时彼刻和观众此时此刻的相遇之中。
周力个展“至近至远”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5
草稿,布面油画,40 × 55cm,2018
草稿,布面油画,40 × 55cm,2018
在《我,我们》(2025)中,周力的绘画中罕见地出现了具体的符号(字面意思上的)。一对拥有体积感的“自画像”形态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并为三段式的构图分割。画面主体似乎悬浮于水面,如同正在孕育中的生命体。在画面中央,一条拥有规则条纹的区域成了底部轻盈笔触和斑驳色块之间的过渡地带——仍有一些未知的可能性等待探索,向内的箭头和向外的箭头符号提示了这种矛盾与共生,“非我”既是“我”,又不是“我”的对立面,世界与个体从未分离。
《我,我们》,布面综合材料,150 x 130cm,2025
最后,让我们借用策展人舒可文援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单向街》里讨论古人与现代人之间差异时提出的说法来结束这篇文章:古代人能投入到一种宇宙体验中,能在与我们最近也最远的事物中感受自身,在狂迷的共同感中同宇宙交流,不像现代人要么盯着具体繁杂之物、要么构造形而上之学。
Related Artists: ZHOU LI 周力
Related Exhibitions: